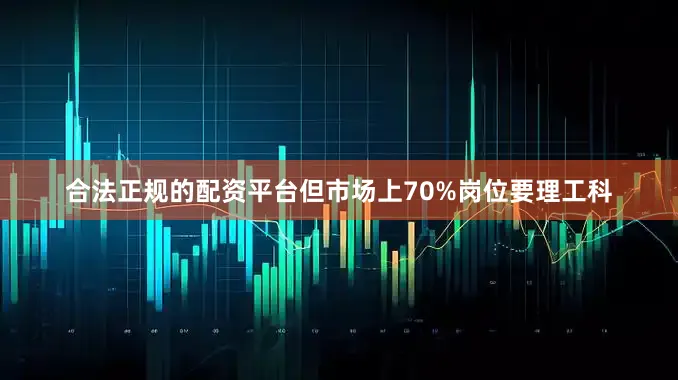1910年,北京克勤郡王府里举行了一场肃穆的仪式。刚满十几岁的少年爱新觉罗·晏森跪接册封诏书,成为清朝第十二代克勤郡王。他头上这顶“铁帽子”,是清朝最显赫的爵位之一,世袭罔替,意味着子孙后代永远承袭王爵,永不降级。
整个清朝近三百年历史,这样的殊荣只给了十二家宗室,晏森的祖先岳托就是清初八大“铁帽子王”之一,曾跟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南征北战,用军功换来这份荣耀。
可晏森接手这顶“铁帽子”时,大清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。王府账面上还有田产铺面,库房里也堆着祖辈留下的古玩珍宝,但年轻的王爷根本不懂这些家底的分量。
他从小在锦衣玉食里长大,满脑子只想着提笼架鸟、听戏喝茶。身边一群趋炎附势的帮闲,整天哄着他“王爷英明”、“祖宗基业厚实”,晏森听得飘飘然,觉得这富贵日子永远过不完。
展开剩余88%仅仅两年后,惊天霹雳传来,1912年2月12日,宣统皇帝溥仪退位,清朝灭亡了。消息传到王府,仆人们惊慌失措,晏森却只是愣了一会儿,转头又逗起了鸟。
他觉得,皇帝退位归退位,咱王爷还是王爷,紫禁城的小朝廷不还在发“优待费”吗?这想法倒也不算全错。民国政府确实承诺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养皇室宗亲,克勤郡王府每月还能领到一笔钱。可这点银子,哪够填晏森挥霍的窟窿?
从王府大门到祖坟石碑
清朝一倒,克勤郡王府的“铁帽子”顿时变成了“纸帽子”。民国发的“优待费”不仅经常拖欠,数额也根本不够支撑王府庞大的开销。
可晏森花钱的手一点没软,下馆子顿顿山珍海味,戏园子包场一掷千金,朋友借钱来者不拒。钱不够了怎么办?他眼珠一转:库房里那些瓶瓶罐罐,不都是钱吗?
王府的老管家急得直跺脚:“王爷!那是康熙爷赏的珐琅彩瓶!乾隆御笔的画啊!”晏森摆摆手:“搁库房落灰有啥用?换钱实在!”于是,祖传的瓷器、字画、玉器,一件接一件被送进当铺或古玩店。
换来的银元叮当作响,转眼又在牌桌酒席上散个精光。没几年,库房就空得能跑马了。
家当卖空了,晏森盯上了更值钱的东西,那座占地几十亩的克勤郡王府。这消息一放出去,立刻引来不少买家。最终,在1916年左右,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出高价买下了这座气派的王府。
签字画押那天,晏森捏着厚厚一沓银票,笑得合不拢嘴。老管家和几个忠仆跪在院子里,对着祖宗牌位嚎啕大哭。晏森却浑不在意:“哭啥?有钱还怕没地方住?”他转头就在城里租了个小院,继续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。
卖王府的钱像流水一样淌走。晏森甚至弄了辆时髦汽车招摇过市,可惜没开几天就撞坏了,他也懒得修,直接扔在路边。等到口袋再次见底时,他的目光投向了京郊,那里埋着列代克勤郡王,坟园里还有值钱货。
他先是派人把坟地上几人合抱的百年松柏、柏树砍了,卖给木材商。接着又把汉白玉的墓碑、石供桌、驮碑的大石龟(赑屃)一块块拆下来,卖给了城里搞建筑的石料商。
最后,连坟头的砖瓦都被扒拉干净换了钱。曾经庄严肃穆的王爷坟,只剩下几个光秃秃的大土包,在风里诉说着荒唐。
“车王”奇闻
王府卖了,祖坟扒了,换来的钱像沙漏里的沙子,转眼间又漏了个精光。到了1931年左右,曾经的克勤郡王晏森,发现自己彻底身无分文,连房租都付不起了。
昔日的酒肉朋友早就躲得远远的,王府的旧仆也各奔东西。他蹲在租来的小破屋门槛上,肚子饿得咕咕叫,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一文钱难倒英雄汉”,更何况他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王爷。
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。晏森环顾四周,发现自己除了身上这把子力气,实在没啥可卖的。
他咬咬牙,做了一个让整个北平城都目瞪口呆的决定,去拉黄包车!这可不是什么体面差事,风吹日晒,跑断腿也只能挣几个铜板。但对于走投无路的晏森来说,这是唯一能混口饭吃的活路。
他跑到车行,租了一辆最破旧的黄包车。车行老板看他细皮嫩肉、说话还带着点旗人腔调,觉得挺新鲜,也没多问。晏森换上粗布短褂,学着其他车夫的样子,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里揽活。
起初,他根本拉不动,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,被客人嫌弃。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,慢慢地,力气也练出来了,对城里的胡同也熟悉了。
然而,纸终究包不住火。他那张脸,他那口京腔,还有无意间流露出的、与普通车夫截然不同的神态举止,渐渐引起了注意。
终于有一天,当他拉着车路过东四牌楼时,被一位眼尖的旗人旧识认了出来!这位前清遗老当时就惊得差点背过气去:“哎哟我的天爷!那...那不是克勤郡王吗?晏森王爷?!您...您怎么拉起洋车来了?!”
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,瞬间传遍了整个北平城的遗老遗少圈子。“铁帽子王爷拉黄包车”,这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,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头号谈资。
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 “车王” ,这称呼里充满了戏谑、嘲笑,也夹杂着几分难以言说的悲凉。每次“车王”晏森拉着车跑过,总有人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。
有好奇打听的,有纯粹看热闹的,也有像那位遗老一样,觉得他丢了整个宗室、整个大清脸面,气得直跺脚骂娘的。
紫禁城里的小皇帝气疯了
消息很快也传进了紫禁城的高墙之内。虽然清朝亡了快二十年,但依据《清室优待条件》,逊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依然住在紫禁城里,关起门来做着皇帝梦。
溥仪身边围绕着一群忠心耿耿的遗老,他们每天都在想方设法维持着皇家最后的体面,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“复辟”。
当“克勤郡王晏森拉黄包车”的丑闻传到溥仪耳朵里时,这位年轻的逊帝气得脸色发白,浑身发抖,在养心殿里直跺脚!在溥仪和遗老们看来,这简直是奇耻大辱!
一个堂堂的世袭罔替铁帽子王,大清最尊贵的十二家宗室之一,竟然沦落到街头拉车,和贩夫走卒为伍?这成何体统?!这不仅丢尽了晏森自己的脸,更是把整个爱新觉罗家族、把已经退位的皇帝、把大清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,都踩进了北平城的尘土里!
溥仪立刻下旨(虽然他的旨令只在紫禁城内有效),严令禁止晏森再拉黄包车!他派人找到晏森,狠狠地训斥了一顿,痛骂他“有辱列祖列宗”、“玷污皇室清誉”。
溥仪甚至从自己那本就不宽裕的“内帑”(皇帝的私房钱)里,挤出了一点钱,派人按月给晏森送去,要求只有一个,老老实实待着,别再出去丢人现眼!
溥仪的这点“救济”,对于习惯了大手大脚的晏森来说,实在是杯水车薪,根本不够他花销。但皇帝的怒火和禁令他不敢违抗。于是,“车王”短暂地消失在了北平的街头。
他拿着那点钱,又过了一段勉强糊口的日子。可这点钱花完之后呢?不能拉车,他又没别的本事,生活很快又陷入了困境。他只能厚着脸皮,四处找昔日的熟人、宗室里的亲戚借钱度日,成了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“穷王爷”。
风烛残年
靠着溥仪那点象征性的接济和偶尔借来的钱,晏森在贫困潦倒中又挣扎了几年。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、挥金如土的少年王爷。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生活的艰辛,让他迅速衰老下去。
他住的地方越来越破,从四合院搬到小杂院,最后只能蜷缩在大钟寺附近一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里。
1939年的冬天,北平格外寒冷。晏森病倒了。没人知道他具体得了什么病,可能是肺病,也可能是其他顽疾。在那个缺医少药、战乱频仍的年代,一个无人问津的落魄王爷,根本得不到像样的治疗。
在一个寒冷的冬夜,末代克勤郡王爱新觉罗·晏森,孤零零地死在了他那间冰冷的破屋里,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终年不过四十多岁。
他死的时候,身边空空荡荡。祖传的王府早已易主,变成了新贵的宅邸或学校;祖坟的石碑石兽早就成了别人家花园的装饰;曾经象征无上荣耀的“铁帽子王”爵位,也随着大清的灭亡化为了历史的尘埃。
他留下的,只有北平街头巷尾流传的“车王”笑谈,以及紫禁城里逊帝溥仪那一声充满愤怒与无奈的叹息。
晏森的一生,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一个王朝彻底崩塌后,那些依附其上的寄生者的必然命运。
他没能像他的祖先岳托那样,用赫赫战功赢得铁帽子;却在王朝覆灭后,用自己荒唐又悲凉的一生,为这顶曾经无比荣耀、最终却沉重无比的“铁帽子”,画上了一个充满讽刺的句号。
他的故事,没有英雄末路的悲壮,只有时代洪流裹挟下,一个被惯坏又无力自救的贵族子弟的沉沦轨迹。
发布于:江西省科元网-配资世界网-牛股策略配资网-无锡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